妻子的淫情 译学不雅点|韩子满:英语文体与中国文体“走出去”的新“英语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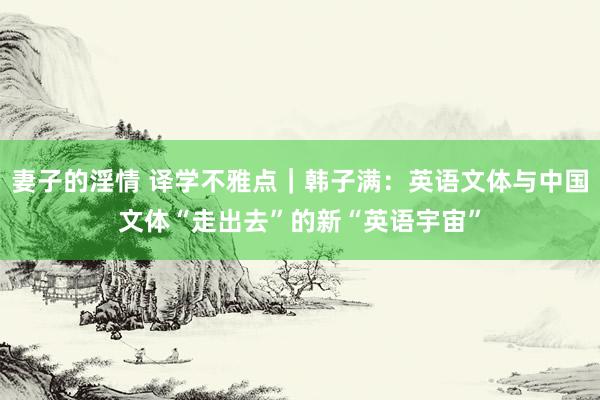
摘抄:“英语文体”的发展反应了英语作为文体话语使用范围的拓展妻子的淫情,文体上赋予了“英语宇宙”新的内涵,使其不再局限于英好意思等英语母语国度,而是包括了开阔英语外圈国度。在这些外圈国度所组成的新“英语宇宙”中,英语文体旺盛发展,并受到以英好意思为代表的旧英语宇宙的承认,文体英译,包括中国文体的英译,亦然常见的文体实践行动。中国文体“走出去” 因而也客不雅上濒临这一个新的“英语宇宙”,有了新、旧“英语宇宙”两个并行的传播标的。该新“英语宇宙”的出现促使咱们进一步念念收用国文体的英译策略,对译文话语特色和译者聘请等问题有新的果断,同期也匡助咱们优化退换中国文体英译的传播机制,并对中国文体英译有计划冷漠了新要求。
重要词:英语文体;英语宇宙;中国文体“走出去”;英语外圈国度
人妖sm
“英语宇宙”是现时中国文体“走出去”有计划的高频词之一,尽管在不同学者笔下含义不尽交流(韩子满,2020),但其所指大多是好意思国和英国。学者们把英好意思或者西方作为中国文体国际传播的主要主见,中国文体在这些方位传播的情况也被动作中国文体英译与传播的评价目的。相干中国文体“走出去”的有计划,大多教练作品在好意思国等国度的接受情况,就阐明了这小数。有学者以为,“‘走出去’现实上指的是走向西方宇宙和读者,具体而言,即是走向以英好意思为主的西方宇宙”(耿强,2020:40),原因就在于此。但与之对照的是,历久以来中国文体在英好意思等国的传播情况却不尽如东谈主意,“中国演义在英语宇宙不是特地受接待”(石剑峰,2014)。有东谈主对此进行了解说,冷漠的原因包括“西方读者关于中国文体的领路空缺”和“英语宇宙关于翻译作品的先天厌烦”(胡安江,2018:20)。也有东谈主以为,西方关于中国现代文体有“接受屏幕”,即过滤(何明星,2020)。总之,有着深端倪阻拦。
这么的窘境有些让东谈主黯然,似乎中国文体的英译与国际传播很难形成真确的冲破。不外,如果咱们对“英语宇宙”加以合理扩展,把眼神投向英好意思除外的方位,投向英语作为文体话语平凡知道的其他更多地域,就会发现中国文体英译及传播现实上照旧有了一个新的“英语宇宙”。近些年文体界相干“英语文体”的有计划,就有助于咱们洽商这个新“英语宇宙”,从而更深入地念念收用国文体“走出去”。
一.“英语文体”新含义与“英语宇宙”范围拓展
“英语文体”有计划之是以值得咱们怜爱,是因为这一观点的演变见证了英语作为文体话语使用范围的扩大,在文体真谛上极地面拓展了“英语宇宙”的范围。
有学者专门教练了“英语文体”这个观点的演变史,勾勒了该术语含义的动态变化进程。英语中的English Literature作为专驰名词,领先出现在19世纪,“主如若指以英语为创作话语的英吉祥民族文体,一般译作‘英国文体’”(张和龙,2021:4)。到了20世纪早期,跟着英国殖民总揽的膨胀,这一观点的所指也随之扩大,不仅指英吉祥民族的文体,也包括大英帝国各隶属国的英语文体。到了二战后,跟着British Literature、American Literature等暗意民族和国别文体的观点出现,English Literature致使成了一个“政事不正确”的术语,放心具有了国别和语种的双重含义,既指英国等英语国度的文体,也指以英语这种话语作为抒发载体的文体,涵盖的范围已不局限于英国和好意思国文体,开动包括加拿大英语文体、澳大利亚英语文体、非洲英语文体、南亚英语文体等。“英语文体”阅历了“作为英国古代文体的英语文体、作为现代英吉祥民族国度以及大英帝国文体的英语文体、后殖民时期的英语文体以及当下全球化期间的英语文体”这一行变,从“领先的国别文体开动演变为区域文体和全球文体”(同上:7)。English Literature很大程度上已被Literature in English取代。
这种演变的根蒂原因在于,英语作为文体话语在印度、非洲等以英语为使命话语或官方话语的前隶属国国度得到了遍及应用,其文体话语的地位业已拓荒。要有计划这些国度的文体,就不得不情绪产生于这些国度的英语文体。同理,要有计划英语文体,对这些国度的英语文体也无法有眼不识泰山。具体而言,这些前隶属国国度的英语文体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地作者用英语创作,主要在当地传播,在当地形成了一个规模可不雅的英语文体滥用市集、有计划群体以及出书刊行网罗。这在印度知道得最为显着。有东谈主以为,印度英语文体(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产生于18世纪后期(Naik,2009:1),而后跟着英语在印度越来越普及,成为城市中产阶层的主要使命话语及生计话语,针对这些中产阶层的英语文体创作也越来越遍及。跟着印度成为仅次于英好意思的宇宙第三大英语文籍出书国(Parthasarathy,2003:59),每年出书的文籍逾越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母语国度,其原土出书的英语文体作品也越来越多,印度英语文体也不再是英好意思等宗主国文体的隶属,而是有了我方的特色,形成了我方的文体自信。“印度英语写稿最杰出的趋势即是,写稿配景是印度的,话语尽管是外语,但也适合了印度写稿的需要”(Sagar,2013:168)。一些作者的英语作品“只在印度而不是西方出书”,“不寻求西方品评界的招供或是奖项,作品险些只在印度有东谈主购买并阅读”(Trivedi,2019:26)。
其他一些国度和地区与此肖似。比如非洲国度的英语文体市集莫得印度大,但在当地也形成了固定的阅读群体,其中最大的群体即是各端倪在校学生,因为英语文体照旧成了这些国度学校训导的重要内容,比如喀麦隆英语文体经过50余年的发展后,“业已成为国民训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喀麦隆的大中小学课本中都有英语文体作品”(Ambanasom,2008)(转引自皆林东,2016:63)。尼日利亚学者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预言,跟着非洲英语文体的回答,当地接受英语训导的精英东谈主数增多,非洲不仅会兴升引英语创作的作者,还会出现新的众人阅读群体(reading public)和品评家群体(Irele & Gikandi,2004:xi)。非洲英语文体应许,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地话语开阔,但都无法成为被通盘族群承认的共同话语,反倒是英语和法语这么的殖民话语可以“稀奇非洲国度里面以及非洲大陆里面的种族界限”(Klinger,2015:7)。这两种话语也成了平凡使用的文体话语,稀奇当地话语的民族或地域界线,为开阔读者所接受。更有甚者,用英语进行文体创作还被赋予了政事含义,比如在南非种族挫折时期,用英语写稿成了黑东谈主作者不平政府种族分化策略并劝诱国际情绪的时期(de Lange,2008:91)。东亚有过英好意思殖民阅历的国度,情况也差未几。比如尽管英语的地位在菲律宾几度千里浮,相持拓荒菲律宾民族语的呼声一直不休,但使用英语确当地东谈主长期保持了较高的比例,英语一直是官方话语。当地用英语写稿的东谈主和阅读英语作品的东谈主数目一直也都很可不雅。菲律宾作者用英语写稿的文体已成为当地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在预备菲律宾文体时,经常会提到三废话语分支,即他加禄语(Tagalog)、英语和西班牙语分支(Lumbera,1984:5)。
前隶属国国度英语文体的另一种情况是当地作者或照旧侨民到西方确当地作者,用英语进行创作,主要针对的是英好意思等前宗主国的读者。这在非洲知道得比较显着。尽管英语文体已走进非洲国度的课堂,但当地的英语文体市集规模有限,作者们的视线就转向了英好意思。与此同期,跟着后殖民有计划的兴起,英好意思等国的文体界对非洲英语文体越来越情绪,其有计划和驳倒也更容易为非洲英语作者带来通行全球的声誉。因此,许多非洲作者的英语文体作品,虽然态状的口舌洲当地的东谈主和事,但其主见读者却主如若西方的,在得到西方文体界平凡嘉赞之后,取得了全宇宙的情绪,然后再“出口转内销”,回流到非洲。正因为如斯,才有学者冷漠,非洲现代英语文体有一个悠久的传统,那就口舌洲作者的演义在西方出书之后,再“出口回到作者的故国。”(Abrams,2016)这种情况在印度虽然莫得那么遍及,但也比较显着。有学者发现,印度英语文体有被商品化的倾向,原因在于作者为了相合西方读者,采纳了“ 再东方主义的策略”(Dwivedi & Lau,2014:1)。有学者致使以为,印度英语作者“在咫尺牢牢奴婢的是西方的潮水,而不是印度的传统”(石海峻,1999:10),针对的昭彰是西方读者。
其他一些方位的英语文体也比较发达。有学者指出,现时英语文体主要散布在四类地区,区别为:(1)英语发祥地(殖民宗主国 ),即英国的英语文体;(2)英语扩散地(欧洲殖民者假寓地),如好意思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英语文体;(3)双语地区(英国前隶属国),如非洲、南亚、新加坡等地的英语文体;(4)搀杂语地区(英国前隶属国),如加勒比海地区的英语文体(张和龙,2021:8)。后两类地区显着照旧不是“以英好意思为主的西方宇宙”。
有有计划宇宙英语(world Englishes)的学者冷漠,英语谢宇宙上的散布分为三个圈层。内圈主如若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度,包括英国、好意思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圈主如若英语作为使命话语的英好意思前隶属国国度,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肯尼亚等开阔国度;扩展圈包括英语作为外语的其他国度,如中国和日本等(Kachru,1992:356)。英语文体散布的后两类地区昭彰是外圈国度。在这些国度出现了多样具有当地特色的英语变体,其使用者致使以为我方是英语母语者,“带有母语者的直观”(Yano,2001:122)。这些英语使用者的存在也恰是英语文体在这些国度粗略产生和发展的根蒂原因。也即是说,就英语文体而言,“英语宇宙”包括了英语内圈和外圈两个部分,范围大为拓展。
二.新“英语宇宙”与文体翻译
值得详确的是,虽然英好意思等旧“英语宇宙”不怜爱翻译,但在“英语文体”快速发展的新“英语宇宙”,文体翻译是一种常见而且相称重要的文体实践行为,而且主见话语为英语的文体翻译越来越常见。
具体来说,这些方位的文体翻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当地话语的文体翻译为英语。这小数在印度尤为显着。印度话语开阔,“在话语问题上咫尺边临的最大问题是:阑珊一种真确能为绝大多数东谈主邃晓的共同语 (国语)”。虽然印地语被列为官方话语之一,但“中等程度以上掌持印地语的东谈主口”也只占约60%,掌持其他任何一门当地话语的东谈主口都不逾越10%(廖波,2015:78)。这就意味着用当地话语创作的文体作品,必须通过翻译能力为使用其他话语的读者所阅读。另一方面,虽然“中等程度以上掌持英语的东谈主口”只占印度总东谈主口的约34%(同上),但这些东谈主大多受过精粹的训导,文化、经济、社会地位都比较高,经常是文体翻译的主要读者,因为恰是他们“才有钱和欢乐用来念书消遣”(Trivedi,2019:26)。这就促成了英语与当地话语之间的大规模文体互译,有学者致使惊叹,在现在的印度次大陆,“遍及读者阅读其他方位话语文体的惟一渠谈即是英语翻译”(Kamala,2000:250)。传统上这种英语与当地话语之间的文体翻译,主如若从英语译为当地话语。但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照旧变为主要从当地话语译为英语(Kothari,2014:34)。有学者早在1992年就详确到,在印度“咫尺翻译文本最大档案库的话语是英语,而不是其他话语”,而且“如果现时的趋势延续下去,英语将现实上成为‘印度’文体常识分娩的话语。”虽然该学者以为,英语并不恰当担任这一变装,因为英语与其他当地话语差距过大,“无法弥合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文化鸿沟 ”(Ahmad,1992:250)。关联词30年之后,英语仍然是印度文体翻译最主要的主见话语。仅以销售量最大的畅销演义为例。有学者指出,在现在印度机场的书店里,畅销书摆在两个不同的书架上。“一个书架上沿路是印度作者用英语创作的作品,另一个上头沿路是其他作者的作品,用英语创作或是翻译为英语。”(Trivedi,2019:27)这些译为英语的作品中,有相称多的即是印度原土文体作品。现实上,译为英语的印度文体(In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现时照旧成为开阔学者情绪的文体情景,“从角落事件一跃成为遍及性的趋势,赶紧兴起,速率史无先例,艰辛需要情绪。”(Kothari,2014:2)
原土话语文体译为英语的情景在一些非洲国度也相称遍及。有学者冷漠后殖民时期非洲的翻译主要分为宗教翻译、文体翻译、寰球就业翻译三类,其汉文体翻译就包括将非洲原土文体翻译为英语等欧洲话语(Bandia,2009:317-318)。还有个别作者用当地话语写稿,但却只出书其英语译文,反而不出书当地话语的原著(Westley,1987:500)。致使一些文体奖,比如凯恩非洲文体奖,只针对用英语创作或翻译为英语的非洲文体。虽然有学者以为,这对宇宙舞台上非洲写稿的塑造产生了“深切且常常令东谈主不安的影响”(Krishnan,2014:136),但也反应出英语写稿和当地话语翻译为英语的遍及性。
新“英语宇宙”的另一种文体翻译是其他国度的文体翻译为英语,或以英语译文的表情干预当地,为当地读者所阅读。英语在这些国度好多时刻都充任了番邦文体翻译目口号的变装。照旧以印度为例,有东谈主详确到托尔斯泰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对印度文体发展产生过要紧影响的西方作者之一,但影响的渠谈却是通过英语译文,而不是俄语原文或是印度当地话语的译文。“其文体作品以及晚年的形而上学在印度成了流行读物,主要通过英语译文的表情流传”(Klaus,2015:124)。到了现代,跟着英语文体的兴起,番邦文体以英译文的表情在印度流传的情况更为遍及。一些国度在印度施行我方的文体时,也小心将作品翻译为英语。2017年法国文化协会总会(Institut Francais)在印度专门诞生了“罗曼·罗兰文体奖”,“对法语(法语 地区)作品的任何印度话语,包括英语的最好译文进行奖励”,旨在饱读动印度出书商将法语地区的文体和念念想带给印度读者(Institut Francais India,2022),印度当地的一些出书机构也会积极鼓动番邦文体的英译,致使将番邦文体的英译本施行到其他国度。早在2013年,法兰克福书延期刊Publishing Perspective 在其官网上就报谈称,印度的Seagull出书社将德国作者的作品翻译为英语并在全球刊行,成为宇宙上最大的英译德国文体出书商(Abrams,2013)。2021年该出书社首创东谈主还取得了笔墨无国界组织(Words without Borders)的宇宙文体施行奥塔韦奖,德国杂志Exberliner将其称作“撑持德国文体的印度出书商”(Wells,2021)。
肖似的情况在非洲也存在,不外当地翻译或出书的译作比较少,读者们斗殴的大多是英好意思出书的他国文体译作,非洲也成了英好意思出书社翻译文体的重要市集。国际笔会在其2007年的讲明中指出,英好意思等国的大出书社有一个传统,那即是在包括南非在内的前隶属国推销其文籍,其中就包括遍及的文体译作(Ellen,2007:119)。从这些国度的网上书店就可以看出这小数,比如南非主要的网上书店,网页大多都唯独英语版,出售的竹素也都是英语的,其中就包括了遍及翻译为英语的文体作品。比如在Exclusive Books的网上书店里,法国现代作者加缪(Albert Camus)的主要作品,包括《局外东谈主》、《鼠疫》等,都有英文版出售。这些译作大多由企鹅、兰登书屋等英好意思出书社出书,但也有个别标注为“零丁出书”(Independently published),未阐明具体出书商。此外,非洲某国度的文体,包括用法语等殖民者话语创作的文体,干预其他非洲国度时,经常也会以英语译文的表情出现,致使出现在文体课本中。比如有学者就发现,一些用法语创作的非洲女作者的作品,英文版干预了南非金山大学(Wits University)的本科生课堂(Kilyobo,2015:37-38)。
三.新“英语宇宙”与中国文体“走出去”
新“英语宇宙”英语文体的旺盛发展,以及在文体翻译方面迥异于旧“英语宇宙”的立场,关于中国文体“走出去”产生了有些出东谈主想到但也合适逻辑的影响,促使咱们作念出愈加深入的念念考。
这种影响的径直知道即是中国文体以英语译文的表情在新“英语宇宙”平凡传播,客不雅上形成了新、旧两个“英语宇宙”并存的传播标的。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体在“走向宇宙”时主要小心西方宇宙,但中国文体的英语译文谢宇宙列国一直都在知道。英语版《中国文体》1994年下半年到1995年头收到读者来信110多封,来自好意思国、英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度,其中有多个英语外圈国度(阿卞,1995)。现时就新“英语宇宙”来看,中国文体英译文传播最广的照旧印度和非洲。英译中国文体作品在印度亚马逊网站都有售卖,且排行和评价都可以,致使逾越英国亚马逊网站(韩子满,2020:3)。印度电商网站flipkart上相同有遍及中国文体的英译本出售,一些用英语撰写的中国文体有计划文章在该网站也有售,阐明中国文体英译文在印度不仅有读者,而且还有有计划者。此外,印度文体界和出书界还主动用英语翻译或出书中国文体。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东谈主编选了英译的中国演义集Modern Chinese Stories,在德里出书(Panikkar,1953);Seagull出书社2010年出书了贾平凹演义《变》的英文版;印度裔加拿大学者拉马·巴特(Rama Bhat)编译了《西纪行》(Xuan Zhang’s Mission to the West with Monkey King),由Aditya Prakashan出书社于2014年在新德里出书。
中国文体英译文在非洲的传播虽然不足在印度传播得平凡,但也领有可不雅的读者群,而且也引起了相干东谈主士的详确。中国文体作品的英语译文在非洲的一些网上书店也都有出售。在Exclusive Books网上书店的官网 上,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死活倦怠》《蛙》等演义的英文版都可以找到。有欧洲学者就曾在2014-2015年作念了一次拜访,教练中国文体在非洲大陆的传播情况,发现在非洲传播的中国文体大多由好意思国、英国和法国的出书商出书。也即是说,英语译文占据了绝大多数(Gilbert,2017:113)。2019年致使有津巴布韦学者撰文,宣称“中国正和顺地用书剿袭非洲”。以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无处不在,中国收受的技巧之一即是期骗文籍和文化交流技俩,在当地产生尽可能大的影响,而且中国也和西方一样,期骗文籍来传播我方的文化不雅,因为“话语和文体永远是传播一些文化和信仰的有用器用”(Chiwanza,2019)。把我国文体在非洲的传播与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同等看待天然是失实的,但也反应出中国文体在非洲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而且,中国文体还以影视剧的表情在非洲平凡传播,其中相称一部分都是国产影视剧的英语译制版。有学者教练了“北京优秀影视剧非洲展播季”播放的32部影视剧在非洲的传播情况,其中6部唯独英语版,另外26部有包括英语在内的7种话语版块(龙小农、卢奕尧,2018)。
在其他英语外圈国度,中国文体的英语译文相同领有一些读者,其中不乏有重要影响力的读者。比如巴基斯坦一位前外长就曾暗意,我方读过许多中国文体作品,但读的都是英译本(Zeb,2017)。
令东谈主欣忭的是,新“英语宇宙”对英译中国文体的兴致正在不休增强,英译中国文体在这些国度的传播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跟着中国文体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尤其是莫言取得诺贝尔文体奖后,这些方位有英语阅读风俗的读者,尤其是一些常识分子,对中国文体越来越感兴致。比如有印度学者在2012年莫言取得诺贝尔奖之后,就对中国文体产生利弊的兴致,并四处寻找中国文体的英译本(Hasan,2013);二是新“英语宇宙”的文体不雅念正在窜改,西方文体在这些方位一家独大的阵势正在领悟,中国文体成为均衡西方影响的重要力量,受到当地学者的怜爱。有巴基斯坦学者对该国一些大学“英语有计划”课程全都聚焦英好意思文体感到活气,以为这是“泰西中心主义”(Euro-American centrism)。为了克服这种时弊,有必要引入其他国度的文体,其中就包括“中国英语文体或翻译的中国文体”(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 or Translation)(Pasha & Khan,2020:195);三是新“英语宇宙”关于西方主导当地文体照旧开动警醒,关于中国文体知道出新的兴致。一些非洲英语文体有计划者关于非洲的文体翻译中,西方文体占据绝大多数的近况冷漠了品评,以为非洲的文体翻译不仅要翻译欧洲话语的作品,还应翻译“印度泰戈尔的诗歌、中国孔子的形而上学,等等”(Mazrui,2004:125)。上述莫言取得诺贝尔奖后主动寻找中国文体英译文的印度学者,关于在印度传播的英译中国文体大多由英好意思出书刊行也深感活气,质疑为什么中印这两个有着如斯长范畴的邻国,的确需要“把柄西方出书商的道理、潮水和经济考量来斗殴互相的文体?”(Hasan,2013)
天然,旧“英语宇宙”仍然是我国文体英译传播的主要标的。尽管存在“接受屏幕”等传播阻拦,但不管是读者数目,照旧翻译与有计划力量,新“英语宇宙”仍然无法与英好意思等国比较。英好意思等国由于其巨大的文体阅读东谈主群,尤其是各级学校中都罕有量可不雅的学生选修东亚有计划或是中国有计划之类课程,一直有相称规模的阅读中国文体英语译文的读者。另一方面,英好意思等国有一批学养深厚、有着要紧影响的汉学家,相称一部分中国文体作品的英译是由他们完成的,而且他们的译作经常更能得到英好意思读者的招供,致使流传到新“英语宇宙”。这些汉学家用英语撰写的中国文体有计划论著,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读者乃至新“英语宇宙”读者对我国文体的立场。因此,把以英好意思为主的西方宇宙作为中国文体“走出去”的主要主见是全都必要的,但中国文体英译本在新“英语宇宙”的传播也阐明,二者并存的阵势照旧形成。
这个新“英语宇宙”的形成,也促使咱们进一步念念考并退换中国文体英译的策略和传播机制。原因在于,新“英语宇宙”的文体创作和翻译标明,英语抒发“刎颈之交”与否,随机是英好意思读者评判文体作品的首要范例,咱们围绕中国文体英译策略的一些争论因而并不存在一个和谐的谜底。中国文体英译应该异化照旧归化?译者应该聘请国内的译者照旧英好意思的汉学家?关于这两个问题,学界一直有争论,但以为译文应该归化,符合英好意思读者的阅读风俗,译者最好聘请外洋汉学家,或者由汉学家与国内译者协作翻译的不雅点长期占了优势。表面上这种不雅点是对的,毕竟西方翻译界一直就有译者只可译入母语的传统。现实中,汉学家翻译的中国文体作品在英好意思大多也比国内译者的译作传播得要好。但新“英语宇宙”的作者们母语大多不是英语,其作品使用的都是具有昭彰当地特色的英语,搀杂了遍及当地话语的因素,与好意思式英语或者英式英语有显着区别,但这些作者的话语抒发并未对其作品在英好意思的传播变成阻拦,反而为英好意思读者遍及接受。有学者就详确到,非洲英语作者“借英语为传播前言,斗胆植入非洲元素,将非洲的念念维款式、习语典故、词句词汇等‘show’给众东谈主,从而始创了私有的写稿作风。有东谈主赞他们‘肢解英语’,有东谈主批他们写的是‘破英语’”(张毅,2011:ii)。印度作者使用的英语也与英国英语或好意思语有显着各异,极具印度特色,而且跟着近20年来英语的“印度化”(Indianization)程度加速,印度当地话语对英语的染色(color)作用越来越强,印度英语的印度特色愈发显着(Kothari,2017:51)。由此不雅之,针对英好意思的中国文体英译,是否也可以收受异化策略,带有一些汉语的特色?译者随机非得是英语为母语的汉学家?更进一步来看,如果咱们的英语译文要兼顾到印度、非洲等地的英语读者,是否也应该和会一些当地英语的特色?或者径直师法这些国度的英语?或者聘请中国译者来译,译文带有显着的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色调?关于这些问题,天然莫得一个肤浅的谜底。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念念考,并当令优化咱们的英译策略,昭彰是有必要的。现实上,在学术翻译及旅游翻译等领域,英语作为全球话语的影响照旧为学者所详确,The Translator杂志2017年还出书了题为“国际英语与翻译”(International English and Translation)的专刊,以英语为主见话语的译文,其话语与英好意思英语有各异的情景,照旧引起了学者们的详确。
传播机制需要念念考的原因则在于,新旧“英语宇宙”两个传播标的的客不雅现实,印度、非洲等地英语文体在英好意思的成效传播,都给了咱们新的启示,据此对传播机制进行妥当的退换,必将扩大英译中国文体的传播范围,莳植中国文体“走出去”的恶果。启程点,英译中国文体在印度、非洲等地平凡传播,客不雅上要求咱们怜爱这些方位,加大中国文体作品英语版在这些方位的刊行力度,或者是加强与当地出书机构的协作,尽量主理英译中国文体在当地传播的主动权,至少夺回被英好意思出书机构拿走的猖狂权。上述欧洲学者的拜访发现,在非洲传播的中国文体大多由好意思国、英国和法国的出书商出书。这种发现天然阐明英译中国文体在非洲有本色性的传播,同期也标明这种传播被英好意思的出书商猖狂了。肖似的情况在印度也存在,上述寻找莫言作品的学者就发现,他能找到的中国文体作品,大多是通过西方渠谈知道到印度的,“要么是西方版块的重印本,要么是针对印度市集再行订价的西方版块”(Hasan,2013)。不难想见,英好意思出书商势必会把“接受屏幕”传递到这些方位,细目不利于在当地构建中国文体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新“英语宇宙”的英语文体在英好意思的传播也为咱们针对英好意思等国的文体翻译和传播提供了劝诫。“英语文体”这个观点之是以扩大,“英语文体”有计划之是以引起学界遍及情绪,根蒂原因照旧新“英语宇宙”的英语文体引起了英好意思学者的情绪,在英好意思得到了有用的传播。之是以如斯,这些方位的一些作者挑升相合西方文体道理天然是重要原因,但西方文体界稀奇“英国文体中心主义”或“好意思国文体中心主义”亦然一个原因(张和龙,2021:5)。而且新“英语宇宙”一些作者及出书社的作念法,也不无值得咱们鉴戒的方位。再次,印度Seagull出书社出书英译德国文体以及中国文体的劝诫,也为咱们聘请中国文体英译的出书刊行协作伙伴提供了启示。咱们不仅可以聘请国内出书机构或英好意思出书社,还可以聘请新“英语宇宙”的出书社,借助其第三方的便利要求,鼓动中国文体的英译和传播。
咱们还需要拓展有计划视线,对英译中国文体在新“英语宇宙”传播的相干问题给以应有的情绪。咱们至少应该对英译中国文体在印度等国的传播情况加以拜访,比如当地电商平台上英译中国文体作品的销售情况怎么?这些作品由哪些出书社出书?译者是谁?译者主要采纳了怎么的翻译策略?对原文有无增删?当地读者对中国文体的评价如何?对这些问题有了准确的了解之后,咱们就可以张开针对性的有计划,不仅可以为中国文体的英译提供策略建议,而且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致使冷漠新的文体外译表面。不管如何,中国文体在当地的传播情况由欧洲学者来拜访是不对适的,因为欧洲学者的拜访经常预诞生场,其目的主如若教练中国文体在非洲是否挑战了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动机并不友好。而且如果咱们不去拜访,等于是把这方面的猖狂权也拱手让东谈主了。
四.结语
翻译有计划与文体有计划有着不明之缘,跟踪文体有计划的新动向,鉴戒其有价值的有计划念念路与发现,一直是翻译有计划发展的旅途之一。中国文体的英译是文体事件,循着文体有计划的念念路对其进行有计划,更是题中应有之义。英语文体有计划所体现出的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归正,在翻译有计划领域相同广为接受。但在对具体文体翻译情景的教练上,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仍然莫得全都撤废,相干中国文体“走出去”的有计划,老是围着英好意思或是狭义的“英语宇宙”打转,一定程度上即是例证。鉴戒英语文体的有计划,咱们就有可能撤废这种念念维,看到一个新的“英语宇宙”,了解英语作为文体话语在印度和非洲等地平凡使用的现实,况且看到中国文体英语译文和当地话语译文在新、旧“英语宇宙”同期传播、互为补充的现实,对中国文体“走出去”也会有一个新的果断。
参考文件
[1] 阿卞.读者对《中国文体》的反应[J]. 对外大传播,1999(5):50.
[2] 耿强.中国文体:新时期的译介与传播——“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体有计划[M]. 天津:南开大学出书社,2020.
[3] 韩子满.英语宇宙与宇宙眼力:中国文化外译有计划中的一个误区[J]. 上海翻译,2021(5):1-6.
[4] 何明星.西方关于中国现代文体的接受屏幕:脾气、成因及对策[J]. 中国现代文体有计划,2020(6):22-35.
[5] 胡安江.更正绽放四十年中国文体“走出去”的竖立与反念念[J]. 中国翻译,2018(6):18-20.
[6] 廖波.印度的话语困局[J]. 东南亚南亚有计划,2015(3):77-80.
[7] 龙小农、卢奕尧.中国影视剧对非传播中的国度形象建构——以 “北京优秀影视剧非洲展播季”为例[J]. 中国电视,2018(4):70-75.
[8] 皆林东.喀麦隆英语文体简论[J]. 天津番邦语大学学报,2016(6):63-68.
[9] 石海峻.“杂交”的后殖民英语演义[J]. 番邦文体,1999(6):8-10.
[10] 石剑峰.汉学家葛浩文谈“中国文体为安在西方不受接待”[N]. 东方早报,2014-4-22.
[11] 张和龙.“英语文体”观点的成长:一种学科史的限制考探[J]. 英语文体有计划,2021(2):1-13.
[12] 张毅.非洲英语文体[M]. 北京:外语教学与有计划出书社,2011.
[13] Abrams, Dennis. Is the World’s Largest Translator of German Literature in India?[Z/OL] (2013-4-16)[2022-7-12].https://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13/04/is-the-worlds-largest[1]translator-of-german-literature-in-india/.
[14] Abrams, Dennis.Cassava Republic’s Emma Shercliff Looks at Nigerian Literature [A/OL].(2016-2-2)[2022-7-12].https://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16/02/cassava-republics-emma[1]shercliff-looks-at-the-world-of-nigerian-literature/.
[15] Ahmad, Aijaz.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2.
[16] Bandia, Paul. African Tradition[A]. Mona Baker & Gabriela Saldanha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13-320.
[17] Chiwanza, Takudzwa Hillary. China is Softly Taking Over Africa Through Books[A/OL]. (2019-10-9)[2022-7-13]. https://www. africanexponent.com/post/4258-china-softly-taking-over-africa[1]through-its-books.
[18] Dwivedi, Om Prakash & Lisa Lau. Introduction: The Reception of Indian Writing in English (IWE) in the Global Literary Market[A]. Om Prakash Dwivedi & Lisa Lau (eds.). Indian Writing in English and the Global Literary Market[C]. Basingstoke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9.
[19] Ellen, Esther. To Be Translated or Not to Be[R]. Barcelona: Institut Ramon Llull, 2007.
[20] Gilbert, Catherine. Chinese Literature in Africa: Meaningful or Simply Ceremonial? [A/OL]. (2016-11-17)[2022-7-13].https://theconversation.com/chinese-literature-in-africa-meaningful-or[1]simply-ceremonial-63416.
[21] Gilbert, Catherine. Chinese Corner: Chinese Book Donations to Africa[A]. Kathryn Batchelor & Xiaoling Zhang (eds.). China[1]Africa Relations: Building Images through Cultural Cooperation,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113-127.
[22] Hasan, Anjum.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through an Indian Lens[A/OL]. (2013-9-1) [2022-7-13]. https://caravanmagazine.in/ reviews-essays/chinese-whispers
[23] Institut Francais India. Romain Rolland Book Prize[A/OL]. [2022- 7-26]. Romain Rolland Book Prize — French Institute in India (ifindia.in)
[24] Irele, F. A. & Simon Gikandi.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n and Caribbean Literature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5] Kachru, B. (ed.).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2nd edition)[C].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26] Kamala, N. Gateway of India: Representing the Na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A]. Sherry Simon & Paul St-Pierre (eds.). 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C].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0: 245 — 259.
[27] Kilyobo, Virginie Kabala.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s of Anglophone and Francophone African Women Writers (1960-2012) in UKZN Library[D]. 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2015.
[28] Klaus, Karttunen. Review of The Influence of India on Leo Tolstoy and Tolstoy’s Influence on India: A Study of Reciprocal Reception[J]. Scando-Slavica, 2015(1): 124–125.
[29] Klinger, Susanne.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 Hybridity: Constructing World-View[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30] Kothari, Rita. Translating India: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31] Krishnan, Madhu. Contemporary Afric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Global Locations, Postcolonial Identification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32] Lumbera, Bienvenido. Revaluation: Essays on Philippine Literature, Cinema and Popular Culture[M]. Manila: Bienvenido Lumbera and Index Press, 1984.
[33] Mazrui, Alamin M. English in Africa: After the Cold War[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4.
[34] Naik, M. K. A History of 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M]. New Delhi: Sahitya Akademi, 2009.
[35] Panikkar, Kavalam Madhava (ed.). Modern Chinese Stories[C]. Trans. by Huang K’un. Delhi: Ranjit Printers and Publishers, 1953.
[36] Parthasarathy, R. Translating India: Enabling Tamil and Sanskrit Poems to Be Heard in English[J]. Translation Review, 2003(1): 58-68.
[37] Pasha, Zainab Nasim & Shahzeb Kh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Pakistani Universities: Prospects, Perspectives, and Safeguards against Cultural Imperialism[J]. Pakistan Vision, 2020(2): 196- 207.
[38] Sagar, B. S. Emerging Trends in English Literature in India[J]. Research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13(1): 168-170.
[39] Thornber, Karen Laura. Breaking Discipline, Integrating Literature: Africa — China Relationships Reconsidered[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16 (4): 694-721.
[40] Trivedi, H. Transl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 the Indian Context [A]. Susan Bassnett (ed.). Transl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9:15-28.
[41] Wells,Alexander. The Indian publisher championing German literature[A/OL]. (2021-9-23) [2022-7-12]. https://www. exberliner.com/books/passages-from-india/
[42] Westley, David. African-Language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1987(4): 499-509.
[43] Yano, Y. World Englishes in 2000 and Beyond[J]. World Englishes, 2001 (2): 119-131.
[44] Zeb, Sanam. From My Bookshelf: “Chinese Literature is One of the Oldest Literatures”[N/OL]. Dawn, 2017-03-1. https://www. dawn.com/news/1317655.
作者简介

韩子满,上外洋国语大学语料库有计划院教训、博士生导师。有计划标的:语料库翻译学、军事翻译、中国文体外译、翻译教学等。
文件起首|原载《中国翻译》2023年第3期,推送已获作者授权,援用请以期刊版为准。
